山河铭记⑧丨中条山殇:晋南豫北的浴血与反思
编者按:抗日战争中,河南作为贯通南北的战略腹地与中原屏障首当敌锋,在烽火熔铸中承载深重苦难,于枪林弹雨中镌刻不屈抗争。从安阳城头鸣响中原抗战第一枪,到竹沟“小延安”点亮信仰星火;从李先念部红旗漫卷豫鄂边,到皮旅奇兵破雾挺进豫西;从花园口滔天国殇映像山河破碎,到军民血肉筑垒的反“扫荡”烽烟遍起原野……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壮举铸就了河南抗战的不朽丰碑。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大河网学术中原秉持“以真实为根基、以学术为支撑、以故事为载体、以精神为灵魂”的理念,邀请专家以理论视角讲述缕析河南抗战事件,再现中原军民身上体现出的伟大抗战精神,让我们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以精神之光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第八期推出《中条山殇:晋南豫北的浴血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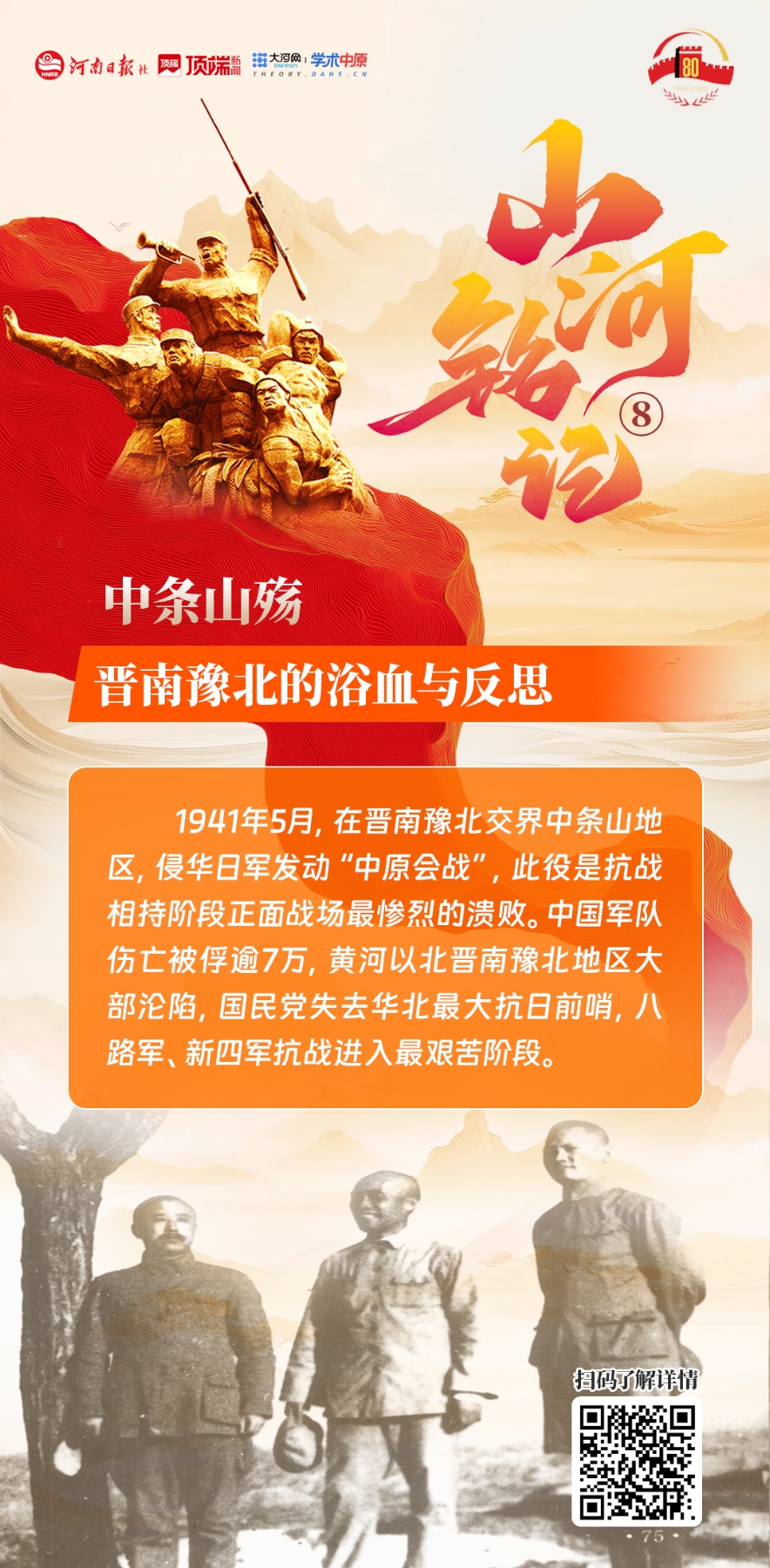
1941年5月,侵华日军集结十万重兵,对扼守晋南豫北门户的中条山中国守军(卫立煌第一战区主力)发动代号“中原会战”的毁灭性攻势。此役是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最惨烈的溃败:约20天激战,中国军队伤亡被俘逾7万人,黄河以北晋南豫北地区大部沦陷。中条山之殇,不仅是军事指挥失误的苦果,更是暴露了战前轻敌、内部协调不畅、军民关系疏离的深层致命隐患。它以山河染血的代价警示后人:民族存亡之际,团结与清醒的指挥是抵御外侮的生命线。

时间轴:1941年5月7日至27日(战役高峰阶段),抗战相持阶段关键节点。
空间轴:晋南豫北交界中条山地区,豫北济源、孟县是东线主战场,此地扼控黄河渡口、屏障关中与中原。
全局关联:此役是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最惨重的失败。其溃败使国民党失去华北最大抗日前哨,日军得以抽调重兵“扫荡”敌后,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在华北抗战中支柱地位的形成过程。对河南而言,战役导致豫北大部沦陷(黄河北岸渡口尽失),豫西、豫西南直接暴露于日军威胁之下,中原腹地门户洞开,后续抗战形势急剧恶化。

一、战略要地沦为“东方马奇诺”幻影
中条山横亘晋南豫北三百余里,扼守黄河天险,是屏障中原与西北的战略咽喉。1938年卫立煌率部进驻该区,掩护洛阳和陇海铁路,多次破坏日军进攻的计划。1941年前后,日军为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紧锣密鼓筹备进攻中条山。5月,这道防线迎来致命危机。
日军为推进侵华战争,亟欲割除华北腹地的“盲肠”,即盘踞中条山的18万国民党军。4月,日军先后调集5个师团、3个旅团及172架飞机,实施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的战略图谋。此时,国民党军内部却发生裂隙:因拒绝反共摩擦引起蒋介石不满的卫立煌被调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指挥岗位,参谋总长何应钦取而代之,“有倾向共产党”嫌疑且被誉为“中条山铁柱子”的第四集团军被调离,由此,中条山西部防御力量被极大削弱。中条山守军及第二战区阎锡山方面都将1941年春以来日军的动向向蒋介石及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作了汇报,但是这种严重情况并未引起相关方面足够的警惕。何应钦错误判断日军进攻意图,误以日军“渡河南下”而调集兵力守河防,未能加固山地纵深防御,为其后迅速溃败埋下伏笔。
二、指挥失灵与英雄绝唱
1941年5月7日,日军兵分三路突袭:东线直扑河南孟县(今孟州市)、济源;北线向董封、横河、垣曲猛攻;西线向闻喜、夏县东南发起攻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针对日军袭击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以切断国民党军联络、封锁山口渡口紧缩包围圈的意图作出指示,命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阻挡敌人攻击及兵力集中。但战区主帅临时换将,指挥部的命令未能有效实施。
中条山战役打响后,东线守军第九军裴昌会部在敌人强攻下步步防御、节节后退,12日,日军占领黄河渡口并西进邵原,完成与中路日军的汇合。西线是日军主攻方向,守军是孔令恂的第八十军、唐淮源的第三军与第五集团军所属的公秉藩第三十四师,7日,日军猛攻阵地,8日突破防线,切断孔唐联系,占领茅津渡等渡口。9日,第八十军遭袭溃败,军长孔令恂弃部渡河,部队伤亡惨重。同时,唐淮源部遭敌人围攻,唐淮源三次突围失败后于12日尖山自戕,其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在激战中重伤自尽。第三十四师阵地失守后退。北线守军是曾万钟第五、刘茂恩第十四两个集团军结合部,日军对两个集团军分割包围,8日即实现中间突破,中条山守军黄河沿线补给线和退路全被截断。东北线守军是刘茂恩第十四集团军、武士敏第九十八军、第十五军及第九十三军等部,在敌军攻击之下,初挫日军。第10日,日军突破垣曲防线,中条山被一分为二,各军不能相互接应、补给中断,被迫北撤。5月12日,日军形成对中条山守军的内外层全面分割包围,随即展开反复扫荡。至6月初,守军残部大多渡黄河突围,中条山陷落。中条山战役之后,日伪占领了其全境的主要交通线、险隘和黄河渡口,直至1945年才陆续解放。
三、华北变局、败因与历史叩问
中条山一役,国民党军损失7.7万余人,牺牲被俘的少将以上的军官达十余人,国民党军主力退守黄河以南,仅存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华北“最大抗日前哨阵地”丧失后,日军控制黄河北岸要冲,抽调3个师团兵力转攻敌后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
中条山战役的惨败,不仅彻底改变了华北抗战格局,更暴露出国民党政权深层的系统性溃败。其一,政治分裂,指挥失序。卫立煌因“亲共”被调离,导致临阵换将、军心涣散,防区周围驻军晋系自保避战,派系各自为政。何应钦取代卫立煌指挥位置后,决策失误致使战端开启后防守被动。其二,后勤保障体系崩溃,战力严重受损。山区补给依赖黄河渡口,然而,战前由于指挥部决策失误导致缺乏粮食储备,造成开战四日全军即告断粮,加剧了日军穿插包围中国民党军的困境。其三,军事痼疾与敌我对比悬殊。日军以飞机、重炮配合进攻,毒气战肆虐,而国民党军不仅装备差,战术亦落后,阵地“长蛇线”无纵深,士兵无训练,遇敌即溃。
中条山战役,既见证了殉国将士的英勇与血气,也反映出统帅部决策指挥的失误,二者共同铸就民族反思的双面镜鉴。八十余载后,中条山的枪声虽已远去,但其历史叩问依旧回响:团结的裂痕终将招致外侮,而一个善于从耻辱中警醒重生的民族,方能真正走出历史的血色黄昏。

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华北战场的关键战役,中国军队在装备劣势下坚守晋南豫北要冲,以血肉之躯阻滞日军南犯中原、西窥陕西的企图,异常悲壮惨烈。这场战役既照见分裂的代价,也见证将士们“宁战死不退让”的决绝。“殇”字既是对惨烈牺牲的铭记,亦隐含对战争教训的深刻省思:中条山战役因战略部署失误、后勤保障不足等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正是这些血的教训推动了中国军队战术改进与民族意识升华。此次战役提醒后人:捍卫和平需要强大的国力与清醒的认知,而抗战精神的本质正是对正义与生存权的执着坚守。

中条山战役留存的历史遗存,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它们不仅是文物与遗址,更是一部立体的教科书,提醒后人:铭记历史不是为了沉湎苦难,而是为了传承勇气、守护和平,在新时代续写中华民族不屈的篇章。
中条山抗战纪念馆。该馆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集中呈现了自1938年3月至1945年8月在晋南大地、黄河之畔,中条山地区抗战英勇事迹。通过对武器残件、士兵家书、军装等实物展陈,战地照片、纪录片等影像资料及复原场景的展示,系统讲述中条山战役背景、过程与影响,尤其注重挖掘普通士兵与百姓的故事。
口述史与档案文献。民间收藏的家书、日记(如将士遗物中的临终绝笔)、地方志中的战斗记录,以及战后幸存老兵的口述史料,为还原历史细节提供了鲜活注脚。
民间记忆与文化传承。代际相传的抗战故事,晋南豫北乡村中,许多家族保留着“祖辈参战中条山”的记忆,通过长辈讲述、村史碑刻等形式延续;部分地区将抗战事迹融入地方戏剧和民歌,以艺术形式传颂英烈精神。
纪念活动与传统。每年清明节或抗战胜利纪念日,当地民众自发前往遗址献花、祭扫;学校与社区开展“重走抗战路”“聆听老兵讲历史”等活动,使革命精神融入当代生活。

《晋豫烽火》,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杨圣清,段玉林:《巍巍中条 中条山军民八年抗战史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景惠西:《中条山抗战实录》,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2005年。
李幺傻:《十万男儿血 中条山保卫战 1938—1941》,西苑出版社,2012年。
卢兴顺,刘波:《悲情中条山 中条山会战影像全纪录》,长城出版社,2023年。
(作者:陈晶晶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编辑: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