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事”知多少⑥丨群众参与+规范管理:新中国初期黄河下游堤防治理的实践经验
编者按: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六年来,从“共同抓好大保护”的嘱托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愿景,黄河流域正书写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今天起,大河网学术中原联合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地域研究与开发》期刊,推出特别策划《“河事”知多少》,“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聚焦黄河历史、黄河文化、黄河水利、高质量发展等关键词,向专家约稿,展示绿色发展理念在河南的落地执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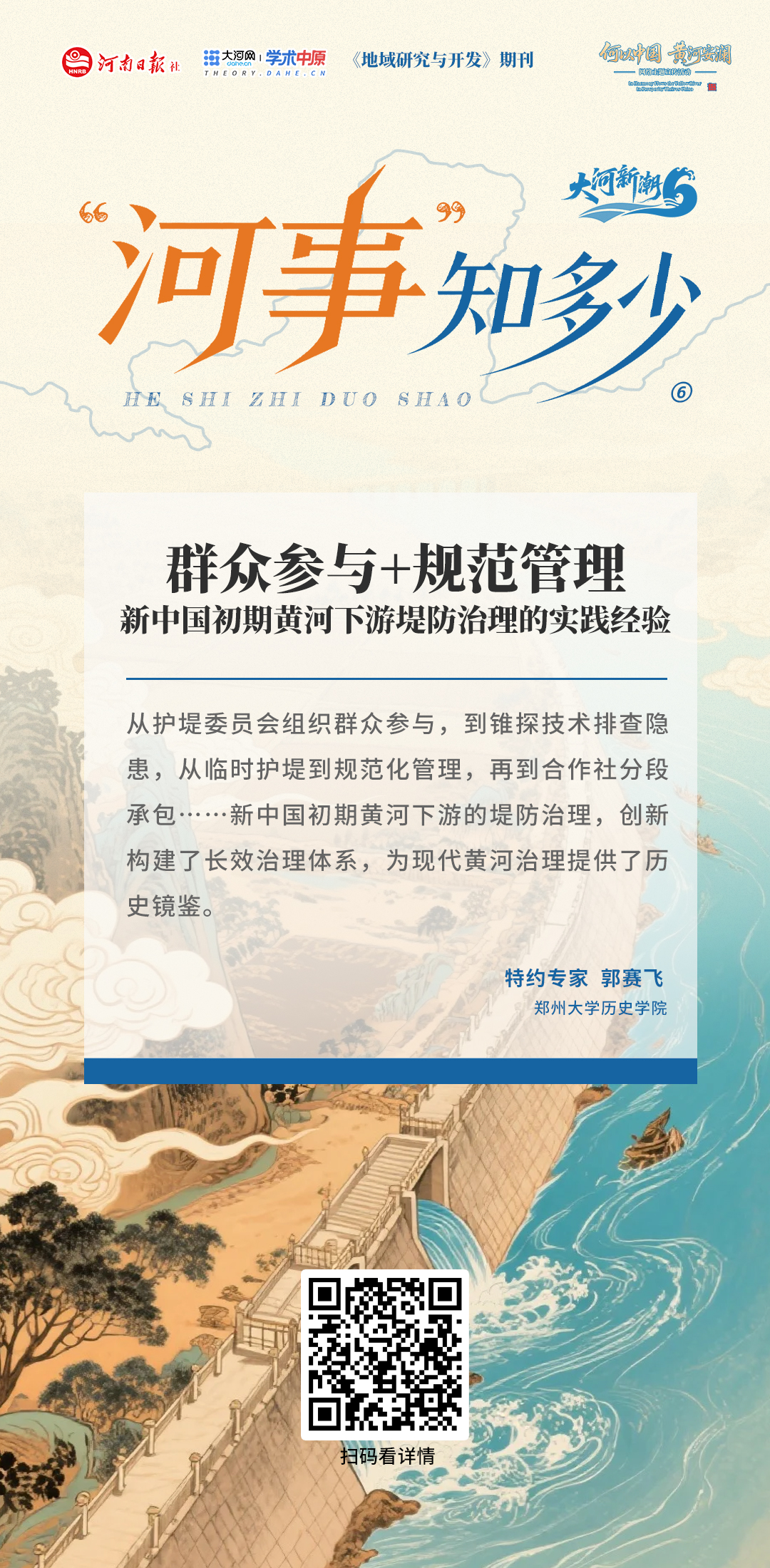
修建堤防是人类应对洪水侵袭的主要方式。在农业社会,堤防可以抵御洪水,对农业生产极为关键,是水利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堤防的维护往往要服从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冀朝鼎指出,在元、明、清三代,相对于防洪或灌溉,统治者们更加重视粮食运输,因此,堤防的修筑与养护都以此为目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黄河发生大规模决口,给华北平原创造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国家亟须对下游大堤进行系统的管理维护。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下游大堤概况
1938年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下游大堤废弃达十余年之久,獾狐洞穴比比皆是。战争年代,各方势力为战争需要在大堤上修筑军沟、洞穴等,造成了极大的隐患。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之后,为保证堤防的稳固,下游地区的防汛工作成为中共的工作重点。冀鲁豫区党委作出指示,要求“沿黄各县将治黄工作作为重要工作之一,领导人民进行治黄抢险,保卫人民的利益”。此后,黄河下游冀鲁豫三省开展了复堤运动。由于当时要应付战争,复堤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而言堤防情况仍不容乐观。此外,当时的黄河还处于分区治理的情况,中共政权还没有能力统一规划下游修防工作,因此,复堤带有很强的临时性。
新中国成立时,豫省黄河沿岸大部分堤防超过20年没有经过系统检查,漏洞引发的风险在1949年汛期集中出现。195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检查发现,大堤在荥阳广武镇到郑州段的9公里内,就有283处獾洞鼠穴,有一处獾洞里面套着好几十个洞,工程队花了七天时间才填好。1949年汛期,堤防的薄弱性充分暴露出来。据王化云回忆,当年大水,一周之间全河出现400多处漏洞,洪水虽未造成大面积的灾害,但临堤的险情层出不穷。他坦言,从这一过程中体会到了固堤的重要。
汛期过后,国家提出了加强堤防建设的水利方针。此后,各地纷纷开展了堤防的岁修工程。但是每年岁修耗资较大,若养护不到位则会减少岁修的成效,这种现象不仅在黄河下游存在,全国都是如此。出于节约资金的考虑,1949年底,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谈到工程的修缮养护,认为如能够注意平日的堤防养护工作,不但可以增强防水的效力,也可以相对减少国家常年岁修的开支。以此为契机,此后的水利工作中,堤防管理工作逐渐得到重视,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
二、护堤组织的成立与演变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复堤运动中,沿黄各地曾设立过护堤组织。1947年,黄河归故后,沿黄冀鲁豫解放区、山东渤海解放区成立了黄河修防处及修防段,普遍建立了护堤委员会,这是较早出现的由政府组成的护堤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沿河地区建立了县、区、村自上而下的护堤委员会,选举固定护堤员,实行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的护堤工作机制。如平原省规定距堤五里到十里以内的村均应划入防汛区,区内各村应建立护堤防汛委员会,有的也称为护堤队或护堤组。
堤防管理工作主要由护堤员负责。护堤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大多是治黄模范或热心参加护堤工作的积极分子。村级护堤委员会成员来自社会骨干,如退役军人、村干部、教师、少年儿童队长及各类模范或热心治河人士。有的还采用护堤、防汛相结合的办法,利用护堤员在汛期代替长期防汛员的做法,使护堤与防汛有效结合。这些人不但有经验和技术,而且在群众中间威信很高。经过长期发展,护堤领导组织逐渐固定化。1955年前后,沿河各县、区、乡相继建立了堤防管理委员会和管理小组,由当地政府负责人兼任管理委员会主任,下设委员若干名。该组织的任务是负责组织、协调、检查、监督管辖范围内的堤防管理工作。护堤委员会还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规定,如会议制度、汇报制度、检查制度、评奖制度等,标志着堤防管理逐渐规范化。
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堤防管理普遍实行由农业合作社分段包干管理的办法。具体而言,由农业合作社确定长期护堤员,并组成护堤班负责管理养护工作。修防段与农业合作社签订合同,明确护堤员职责,以及堤上收益与护堤员报酬的分配办法。一般情况下,由社队选派护堤员负责堤防管理养护工作,堤草树柴收益归农业社,社对护堤员实行评工计酬参加农业收益分配。这种做法有利于减轻社队堤防管理负担,增加收益。群众订立合同后有了更明确的目标,护堤积极性被广泛调动起来。如有的群众说:“黄河是国家的,我们应当看护,同时还有一部分收益是一举两得的事。”
三、捕捉害堤动物发掘大堤隐患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上的黄河决口,半数起源于獾狐洞穴形成的漏洞。有清一代,沿黄各地对堤防越来越重视,每个汛期专门设置獾兵,负责捕獾。近代以后,频繁的战争与自然灾害为野生动物进入农耕区提供了机遇。由于黄河堤防在战争时期未能得到有效管理,大堤成为獾、鼠隐匿的重要场所。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害堤动物的认知发生了变化,除了强调它们的危害性,也提出了利用的观点。如武陟修防段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时,专门介绍了捕獾的好处。除了獾以外,当时还有一种主要的害堤动物,即鼹鼠,这一动物的特点是擅长打洞,一天能掏洞七八丈,根据1950年河南省锥探大堤的统计,80%的洞穴是其造成的。
这些洞穴的存在使得黄河大堤形成了千疮百孔的状态。翻修大堤时这一现象更加明显,如修防队在利津县潘马庄百余米的堤段上,就发现50余个洞穴,大的直径达二三十厘米,把大堤切开后形同用刀切开的藕一样。而这些漏洞,如不彻底地及时翻修,很快便会形成新的洞穴。如山东归仁区的一个獾洞在堤顶下方一米的距离,由背河一直通到临河,每年都要挖填,已修补四次。可见,发掘大堤隐患并开展彻底的翻修工程对于固堤来说十分必要。从1950年起,黄委组织在全河开展了消灭大堤隐患的活动。
即使民众与河务局创造了许多捕捉害堤动物的办法,但效率较低且较为分散,而锥探技术的发明与普及为全面消除大堤隐患创造了条件。1951年,封丘修防段工人靳钊发明了利用钢锥探摸堤身隐患的办法。由于堤线较长,锥探队需要先向附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选择重点的可疑的地方钻探,才能更快地发现隐患。工程队员和长期防汛员组成的锥探队,每到一个村,首先由村干部召开村民大会,讲解漏洞对大堤的危害,并用历史上因洞穴决口的具体案例说明隐患的危险,而后深入群众做堤身洞穴情况的调查,以便有重点地进行工作,同时发动群众自报人造的洞沟。此外,还组织群众参观打出挖掘后的洞穴,并当场进行具体的宣传。群众看了大洞后说:“共产党做啥都有办法。”“很易接受。”锥探技术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治黄工作的重大创造之一”,实施以后“三个月内即消灭隐患六百余处”。后来该技术不断发展,由单人行动变为多人合作,又从人力过渡到机械并在全河广泛应用,大幅提升了发掘大堤隐患的准确度和效率。
为发动群众参与发掘大堤隐患,河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检查与奖惩办法。由于堤坝中的隐患普遍比较隐蔽,如不发动群众很难发现。为了提高群众自报隐患的积极性,山东省提出要把消灭隐患发展成群众性运动,并颁布了具体的奖惩办法。1951年,山东河务局制定出《民房堤段隐患重点检查办法》和《消灭堤防隐患各种奖励及赔偿修正办法》,规定凡自动报告本人堤上房屋内隐患的,经查属实,除了给予奖励外,还补助因翻填导致房屋损坏的费用。密报民房内重大隐患的,按照险情大小,奖励25~50公斤小米。对于自己房内有隐患隐瞒不报而被他人检举的,拆毁房屋不发拆迁费。此后,这一工作逐渐走向技术应用与群众运动的结合。
除此以外,政府为鼓励群众捕捉害堤动物制定了奖励办法。1949年6月,黄委驻汴办事处规定在大堤两旁各1公里内,捕1只獾,奖励5斤小麦。在堤身捕1只地鼠,奖励1斤小麦。捕获獾后将蹄子截掉核验发奖后,兽肉和兽皮归捕捉者所有。武陟沁河修防段提出捕捉大獾奖励20斤米,小獾10斤米。在这样的鼓励下,群众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提高,如武陟县北归善一组不到三个月每人捉獾的奖励及修堤的工资达600多斤小米,售卖獾油狐皮等还能得到另一份收入。随后1955年新币发行,奖励逐渐由实物过渡到现金。这样的奖励办法,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捕捉獾狐和锥探大堤在当时还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群众发明了诸如此类的口号:“前方打美帝咱也是打仗,逮住一个獾就等于消灭一个美国鬼子。”“发现一个洞穴,等于消灭一个美国鬼子。”
在物质奖励与政治鼓动之下,群众性检查大堤隐患的工作成效显著。各地成立各种打獾小组,捕捉獾狐。锥探技术与群众自报隐患相结合,大堤中许多暗藏的洞穴也被发掘出来。最能体现发掘隐患工作成效的是1954年汛期,当年的洪水无论从洪峰、水位、洪水总量还是高水位持续时间来说都超过了1949年,但全河仅出现了一处漏洞。
四、植树植草绿化堤防
在大堤隐患被逐渐消灭的过程中,以植树植草为中心的堤防绿化也逐渐展开。因柳枝不易腐烂,是天然的河工物料,明初开始河官便提倡在沿河种植,并总结了多种植柳办法。最初治河以民柳为主,官柳作为民柳的补充。但随着用量增大,民柳逐渐不够使用,于是17世纪中叶以后,河工用柳大半靠官柳。明清时期偷割堤草、砍伐堤柳、偷盗堤土相当严重,形成官办大堤与群众无关的局势。近代以后,政府继续倡导在河边两岸植柳,但因并无专项资金且政局动荡,成效并不明显。
新中国成立以后,林垦部提出“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与利用”的方针。在大堤上植柳,不但有利于巩固大堤,为险工提供材料,更被赋予了调节气候、阻挡风沙以及保护农作物的环境意义。河务部门对大堤植树制定了规范的制度。1948年渤海行署、河务局联合发布训令,“为了保护堤身,巩固堤根,应予内外堤脚二丈以内广植树木,禁止耕种稼禾,以期保证大堤稳固”。1949年公布的《渤海区黄河大堤植树暂行办法》限定了植树的品种与大堤保护范围,规定植树种类以柳为标准,其他树株一般不栽。并要求无论平险工,在大堤堤脚外二丈以内一律不准耕种其他谷物。该做法明确了周边土地的所有权,有利于保护大堤。
在树种的选择上,除了柳树以外,河务局开始提倡树种的多样性,由过去单纯的防御型转变为生产防御相结合。根据大堤内外不同区域的特征种植不同的植物。在树种的选择上,因高柳成活率较低,并且不好发芽,一般选择卧柳,卧柳属于丛生,成活率较高,三年之后,就能将枝条砍下来作为固滩或抢险的物料。此外,河南河务局计划在背河大量栽植建筑用材和果树,如白杨、苹果、梨树等,将大堤变成生产的大堤。据1956年统计,河南黄河大堤已栽植果木树和其他杂树32万余棵。根据绿化黄河大堤工作的规划,堤顶上除留交通道外,两侧要栽三行或两行的果木树,背河要栽各样的杂木树。树种的多样性与广泛种植提高了大堤植被覆盖率,重建了大堤的生态环境。
绿化大堤与堤边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群众在绿化大堤中创造出许多经验。濮阳县的群众,在大堤上开展种植葛芭草的试验。沿堤群众流行着一种民谚,“堤上种上葛芭草,哪怕雨冲溜来扫”。新草种的推广解决了过去不好植和难找苗的顾虑。植树与植草等护堤工作为沿河民众提供了额外的收入。当时大堤树木采取国家和群众合营、收入分成的办法,树头和树根归群众所有,树身四六或五五分成。一个村子如果管护几百米大堤,这些柳树可以为村庄提供烧柴和饲料。
在护堤与切身利益关联以后,沿河群众对护堤的参与度明显提升,护堤的成效越来越明显。根据黄委会调查,自1949年提出堤上的收益,包括草、柳枝及柳荫地的农作物归个人所有口号后,濮阳县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完成了两万余棵的植柳任务,且成活率达90%以上。柳树不但长势茂盛,而且排列十分整齐。1952年一年河南、平原两省植草共计堤线估占两省全部堤线长度的78%。每人每日最高效率达700丛,最高成活率达95%,最低也有80%,大堤已经开始成为绿堤。
堤防的管理是维持黄河下游河道稳定的关键环节,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保证下游安澜,国家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维护堤防稳定。堤防管理组织逐渐完善,沿河各地吸收地方积极分子成立了护堤委员会,形成了初步的护堤制度。在农业合作化的影响下,护堤工作逐渐同沿河各地的中心任务相结合,渗透进沿河村庄的日常生活。在具体措施上,地方政府将群众运动与技术应用相结合,鼓励群众捕捉害堤动物并给予奖励,广泛推广锥探技术。在这一过程中,野生动物逐渐退出了黄河大堤,伴随着大规模植树植草运动,黄河堤防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的堤防管理在组织、制度与技术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为确保黄河下游大堤稳固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结
在新中国初期黄河下游堤防治理的实践经验表明,组织群众参与护堤委员会,结合锥探技术排查隐患,既降低成本又激发了群众护堤主动性;临时护堤到规范化管理,再到合作社分段承包,制度创新构建了长效治理体系。这一经验启示现代黄河治理可强化跨区域协作,将工程措施转化为常态化管理,并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监测效率,延续群防群治传统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
【作者:郭赛飞 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黄河下游滩区治理研究(1949-2022)》(23CZS081)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付婷

